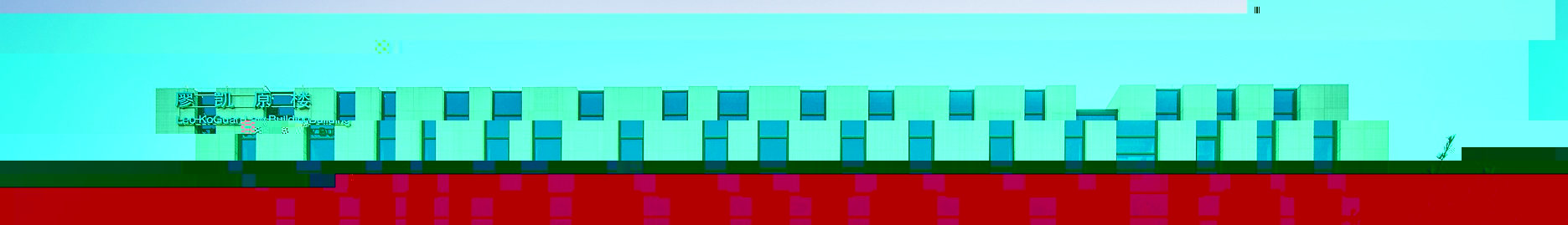必須注重培養司法人員從海量數據當中發現法律适用難題的能力;在大數據應用當中必須全面收集作無罪處理的案件數據,要克服這一類案件數據過少帶來的局限;需要從現在起重新形成關于量刑的大數據。
應該對數據提供的“有限知識”保持反思的能力,對類案當然要關注,要盡可能去檢索和比對,但是又不能絕對依賴于類案,尤其是絕對不能迷信關于量刑的類案,要帶着反思和挑剔的眼光審視類案,盡快尋找到類案檢索的着力點,強化這方面的工作。
在刑事司法過程中,數字時代對司法活動帶來巨大沖擊,也為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實現提供了巨大支撐。就起訴、裁判結論的形成而言,數字時代的司法活動有自身的特點。數字時代積累了海量的信息,獲取數據信息很容易,大量裁判文書上網,檢察官、法官裁判必須要保證案件辦理盡量和之前的同類案件處理結論相協調。此時,大數據的運用就很重要。實踐中,同案大緻同判的現實需求很強烈,因為基本相同的案件如果處理結論差異很大,就很容易成為批評的對象。因此,今天的司法活動已經習慣于從海量數據中檢索類案進而形成起訴或判決結論,其中用得最多的是通過類案檢索為量刑提供輔助和支撐,依靠大數據使量刑更加“有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也從司法文書中提煉并發布大量指導性案例或者典型案例。确實,現在離開大數據來開展刑事司法活動已經不太可能。
與對司法大數據的運用相匹配,有的司法機關建立了類案強制檢索報告制度,依托某些法律法規檢索系統和中國裁判文書網、人民檢察院案件信息公開網等官方載體,以“相似的情形相似的處理”為基本内涵,通過對高質量、代表性、典型性、指導性案例的學習研究,為法官、檢察官辦案提供參考,尤其是要求司法人員辦理“重大疑難複雜和新類型案件”必須執行類案強制檢索報告制度。所以,誰也不能否認,數字時代的大數據确實為刑事法治的實現提供了技術支持,其存在有獨特價值。
但是,目前在刑事司法領域對數據的應用也還有一些值得我們關注的地方,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從海量案例中遴選出來的指導性案例或者典型案例的指導性還不強,其作為類案所能夠提供的指引作用還需要進一步加強。第二,有不少無罪判決和不起訴文書沒有全面公開。第三,同案大緻同判的實現存在客觀障礙,之前形成的海量數據當中存在一些問題,尤其是量刑過重的問題值得特别關注。
針對這三方面的問題,未來刑事司法領域要實現法治,應當充分關注和避免當下類案檢索的局限性問題。為強化類案檢索工作,至少要特别關注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必須注重培養司法人員從海量數據當中發現法律适用難題的能力。現在大量的指導性案例,無論是最高人民法院的還是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其挑選存在兩種比較明顯的傾向,一是挑選的案例當中,大量屬于重申司法解釋型的,司法解釋之前有什麼規定,就此規則适用挑選一些案例來支撐、印證司法解釋。這部分指導性案例和典型案例特别多。另外一部分案例展示了檢、法兩院服務社會經濟大局的能力和業績。這些指導性案例當然可以編選。但是,在此之外,我們要重視挑選能夠提升法官檢察官的裁判說理水平、能夠發現法律适用難題的一些案件。這樣的案件目前太少,如果不重視這類案件的挑選,今後可能無法形成更多有指導價值的先例或者類案。而這些案例太少背後提出的問題就是:司法機關确實應該考慮增強文書的說理,目前如判決書以及不起訴決定書的說理都很不透徹,必須下大力氣解決這個問題。
目前大量的刑事判決,在“本院認為”部分表述的理由特别簡單,标準的表述是根據刑法分則某一具體條文的規定,實施某種行為的構成某罪;然後進一步展開說被告人的行為符合某條規定,辯護人的辯護意見沒有事實和法律根據不予采納。法官和檢察官似乎都相信講得越少越不容易露出破綻,越不會被人挑出毛病。這樣的心态之下很難寫出很好的司法文書。司法文書的說理問題如果不解決,今後,我們要形成一系列的指導性案例或者典型案例就很困難。這會使得大數據對未來司法公正的支撐變得非常有限,很多改革措施很可能原地打轉,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如果要從法官檢察官的司法說理能力當中去發現法律适用的難題,那麼我們同時也要關注一些罕見案例。這些罕見判決當中有能夠改變裁判規則的情形。就是有些案子我們以前可能一直都這樣判,但是,以前那樣判的思路有可能有疑問,現在突然出現一個判決,改變了原來的裁判規則。那麼這樣的一個判決如果它講理很充分,言之成理,雖然跟原來的先例不一樣,但是這樣的判決也要尊重。罕見的案件改變裁判規則之後,學者對其要尊重、研究,法官檢察官要遵從。所以,在大數據時代必須關注海量的數據,從中可以發現司法規律,尋找社會治理的契機,但是,小樣本的罕見判決也很重要,它可能構建新的裁判規則,甚至帶來法學知識發展的增量。
第二,在大數據應用當中必須全面收集作無罪處理的案件數據,要克服這一類案件數據過少帶來的局限。實踐中法官判無罪很難,檢察官作不起訴也比較困難,有的案件确實法律關系比較複雜;被告人的行為有一定的危險性,維穩的壓力、地方保護帶來的一些現實考慮都使司法上作無罪處理很困難,所以我們看到的大量案件都是有罪判決。無罪的判決在近幾年“兩高”的報告裡經過統計大概萬分之五左右,這是非常低的一個比例。
有些無罪判決、檢察機關作不起訴的案件,在最高法的裁判文書網和檢察機關的不起訴文書裡都可能查不到。那麼,作無罪處理的數據少,會給人一個感覺:有一定危險性的行為或者待處理的行為很可能都應該作有罪處理。這使得辦案人員有時候要找一個無罪判決來和自己手上的待處理案件相對照很困難,律師的無罪辯護也很難。比如說對于知假買假索賠的行為怎麼處理在民事上存在争議,但是刑事上基本上都作有罪處理。偶爾有一些無罪判決,但這些無罪判決并未出現在公開的網絡中,進不了大數據的系統。所以,确實要下大力氣去關注無罪判決數據庫的建設問題。
最後,需要從現在起重新形成關于量刑的大數據。在以往的刑事司法數據裡,關于量刑的數據體現出來的案件處理結論都是量刑畸重或至少是偏重的,因為最近幾十年來開展了一些打擊刑事犯罪的專項活動或系列活動,使得量刑活動總體上“高位運行”,所以,如果要對以前的類案數據加以運用,在量刑這個問題上就要特别慎重。特别是在檢察機關推行認罪認罰從寬處罰以後,很多案子都應該處理得比以往更輕,适用輕刑、宣告緩刑的案件應該大幅度增加。所以,檢察官提出量刑建議以及法官在實際量刑的時候,如果想參照“先例”或類案的話,判刑過重這個問題需要特别關注,必須将認罪認罰從寬的因素加進去考慮。
總之,數字時代的刑事司法享受了大數據帶來的各種便利,類案檢索是大勢所趨。但是,也應該對數據提供的“有限知識”保持反思的能力,對類案當然要關注,要盡可能去檢索和比對,但是又不能絕對依賴于類案,尤其是絕對不能迷信關于量刑的類案,要帶着反思和挑剔的眼光審視類案,盡快尋找到類案檢索的着力點,強化這方面的工作。
(本文是作者于2021年5月9日在中國行為法學會、中南大學beat365聯合舉辦的《中國法治實施報告(2021)》發布會暨“數字時代的法治實施”專題研讨會上的主題演講内容,此次發表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