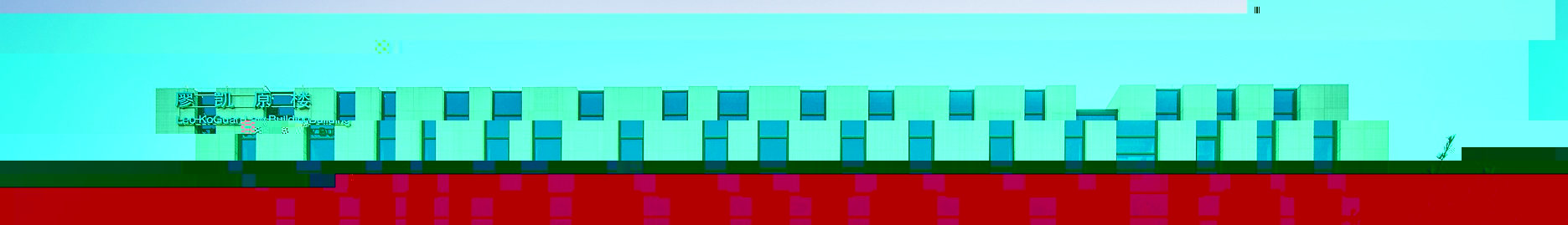【摘要】實踐中,行為人主張債權或其他财産權利時使用恐吓或欺騙手段的情形并不少見,司法人員面對這類案件極易産生定罪沖動;理論上的多數說認為這類行為符合财産犯罪的構成要件,僅可能阻卻違法。這些立場都值得反思。定罪範圍過寬的實務操作與财産犯罪的本質并不相符;依靠私力救濟這種(超法規的)違法阻卻事由解決涉及權利行使的犯罪認定問題,等于沒有給被告人“出路”,在我國當下不是理想的方案。為此,從構成要件符合性的角度切入,根據整體财産損害的邏輯,認為主張權利的行為不會給對方造成實質的财産損害,從而在違法性判斷之前就否定行為的犯罪性,從邏輯上講得通,也更為務實,能夠遏制近年來将主張權利的行為大量認定為敲詐勒索等罪的司法趨勢。基于請求權基礎而恐吓對方的,由于從一開始就不可能造成實質的财産損失,實行行為性、非法占有目的等也都可以被否定。在權利存在争議,以及行為人自認為在拆遷補償等事項中“吃虧”,使用舉報、向媒體揭發等恐吓手段提出較高賠償要求等情形中,隻要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權利根據,對相對人的交付就不應評價為産生了财産損失,被告人不應構成敲詐勒索等财産犯罪。使用暴力、威脅手段索要債務,其濫用權利的手段行為構成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等其他犯罪的,按照相應犯罪處理。
【關鍵詞】權利行使;違法阻卻;财産損害;敲詐勒索罪;法秩序統一性
【本文來源】《現代法學》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