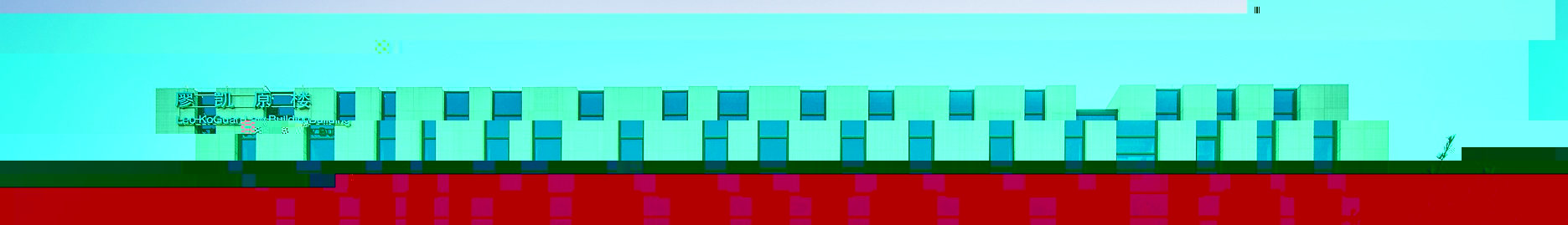本文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全面推進嚴格公正司法,努力讓人民群衆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刑法學讨論犯罪和刑罰問題,建構科學合理的犯罪論體系,實現妥當的處罰,對于推進公正司法、實現社會正義具有重要意義。刑法學的建構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形成符合社會發展要求、助推刑事司法公正的學科體系。要實現中國刑法學的自主化、本土化,需要明确關注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結合中國的立法和司法實踐,基于中國問題展開研究。應當說,我國近年來關于刑法學的研究已經比較注重融入“中國元素”,展現了刑法學的中國特色,從而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創新,這也是我國刑法學研究最近十多年的實質性進展。這至少體現在以下方面:第一,學派研究中的“中國元素”。如果想要形成刑法學的“中國學派”,就必須對國外的刑法學術論争史、發展史進行深入研究,這方面在最近二十年取得了豐碩成果。陳興良教授就曾指出,雖然行為無價值論和結果無價值論本是日本的一個學術話題,但其被引入我國刑法學界以後,我國學者并沒有停留在對此的介紹上,也沒有完全重複日本學者的争論,而是結合我國刑法中的理論問題與實務問題,進行了具有相當深度與廣度的研究,對于促進我國刑法理論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第二,在反思中國審判實踐中,對建構合理的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判斷規則的深度探究。第三,根據刑法分則中的具體犯罪,如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受賄罪、介紹賄賂罪的關系等,思考正犯與共犯問題。第四,結合分則中對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逃稅罪、侵占罪、聚衆鬥毆罪的規定等,思考客觀處罰條件問題。第五,結合刑法分則在詐騙罪之外大量規定特殊的金融詐騙等罪的具體情形,深入思考法條競合、想象競合犯的關系問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研究進展為形成中國的刑法教義學奠定了良好基礎。
總之,不能将中國刑法問題與外國的問題同質化,特别是不能用外國刑法的理論以及立法規定生硬地解決中國的現實難題,無視現實問題的背景和制約因素,這一點在共犯論、未遂論中表現得特别充分。此外,有的現實難題确實難以從外國的理論中尋找到答案,這一點在信息網絡犯罪中表現得特别充分;解決有的難題不能超越中國發展的曆史階段,例如,完全按照國外的不作為犯理論來解決中國實務難題,或者簡單地主張借鑒外國某項現成的刑罰制度,不顧及我國的法律制度體系,顯然不是可行的思考方法。中國刑法學完全有可能在對大陸法系不法論發展曆程中的正反經驗加以甄别和總結的基礎上,以本國的刑法規範和司法實踐為土壤,構建符合自身時代需要的不法理論乃至犯罪論體系。從犯罪論擴展開來,逐步形成有别于德日的刑法教義學知識體系當然是可以期許的。
第二,要建構本土化的中國刑法學,并不意味着要排斥國外合理的刑法學研究成果。歐陸刑法學有二百多年的規範發展曆史,其刑法學理論大多經過無數學者“前赴後繼”的反複争辯、打磨,對很多問題也能夠給予妥善處理。因此,作為刑法學研究的“後發國家”,我們應當充分認識到自身理論的“先天不足”,必須承認實質問題的共通性或相似性,進而接受跨越國别的刑法學理論共識和一般方法論,借鑒、引入國外理論并不意味着我國刑法學自主性、主體性的喪失。為此,要仔細甄别域外教義學知識與中國刑法語境的兼容性,積極引入沒有語境障礙的教義學知識,借鑒其合理成分,并運用教義學的一般方法創造立足本土的新型教義學體系。
第三,要避免将學術觀點做絕對化、程式化對立,充分關注刑法問題的複雜性。刑法學者應該保持更為從容、緩和、成熟的心态,要能夠兼容并包,避免憑直覺“選邊站隊”,做到“君子和而不同”。例如,将刑法學中的思考單純地歸納為“結果無價值論”與“行為無價值論”之間對立的做法,就過于簡單,不具有建設性。其實,刑法中有很多修正理論都是為了防止問題絕對化而提出來的。例如,關于主觀要素的定位,行為無價值論承認主觀違法要素,用以揭示行為所具有的客觀危險,而部分結果無價值論者為了處理特殊問題的便利,也例外地承認主觀違法要素,還有的學者認為違法并非純客觀的,隻根據客觀方面就能夠判斷法益侵害的危險性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說作為主觀違法要素會有認定上的困難,但在責任階段考慮主觀要素也同樣困難。内心事實的認定如果作為違法要素就困難,如果作為責任要素就容易,這是不可能的。這揭示出兩種理論在相關問題上的對立已經部分消解。因此,對于刑法教義學的長遠發展而言,要緊的不是理論上的程式化對立,而應站在相對超然的立場上,通過着眼于現實個案的妥當解決來形成體系性思考,至于給這種解決難題的方法論貼上何種學術标簽倒是次要的。
第四,對中國刑法立法應當有足夠的尊重,不宜動辄批評立法。我國在1997年大規模修訂刑法之後,最近二十多年來,又制定了十一個《刑法修正案》。在功能主義背景下的刑法立法活躍化趨勢,是刑法學者必須面對的現實。對此,也有學者提出質疑,認為我國有的刑法立法是情緒化的,有的規定是虛置的。這種批評未必站得住腳。我國活躍化的立法始終關注轉型社會的現實問題,其具有實證基礎,保持了立法的明确性和處罰的輕緩化,因而具有合理性。立法意味着平衡和決斷,其與刑法教義學主張體系合理、解釋上盡量沒有漏洞等在方法論上原本就不同;如學者先預設出一個刑法思想的分析框架,再去批評為完成現代社會治理任務而制定的刑法條文,屬于意義有限的“跨界”對話;立法的實際效果不會因為刑法學的批評而消失;過度的立法懷疑主義勢必從一開始就将刑法理論和立法實踐對立起來,遏制了刑法教義學對未來的立法科學化産生具體影響的機會。立法活躍化為刑法教義學發展帶來新的契機,在教義學上從體系性建構轉向問題思考,對立法所提出的難題予以充分展開,尤其是對構成要件進行合理解釋,對犯罪競合關系做細緻梳理等,都能夠增強刑法教義學的“應變”能力。在立法活躍化時代,刑法教義學必須盡快實現觀念論的轉變和方法論的拓展。
歸結起來,我國刑法學研究者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刑法學知識具有根深蒂固的國界性和地方性,因此,刑法學要以當下的中國刑法典為研究的邏輯起點并受其嚴格約束,堅守罪刑法定原則,處罰盡可能趨輕,特别要注意避免量刑失衡。要真正構建中國的刑法學,就必須喚起研究者的主體意識。讨論者關心的問題應該是立法者對法律争點已經給出了什麼樣的答案,而不是立法者應該給出什麼答案。因此,在建構刑法學時要特别注重思考哪些問題是中國立法、司法上特有的問題,或者該問題在外國雖然也存在,但在中國表現得更為特殊;哪些問題是中國的真問題而非僞問題。在發現問題的基礎上,未來的刑法學不能僅滿足于對既有國外的刑法理論進行“小修小補”,而應當實現更大規模的、更有深度的、與中國司法現實更為貼近的創新。我們必須按照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要求,尋找能夠更好地與中國的立法、社會現實、法律文化相對接和匹配的,更加具有說服力的問題解決途徑,而不是一味地用中國實務上發生的案件去印證歐陸刑法理論的妥當與否,從而逐步實現中國刑法學研究的創新,為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貢獻刑法學研究者的微薄力量。